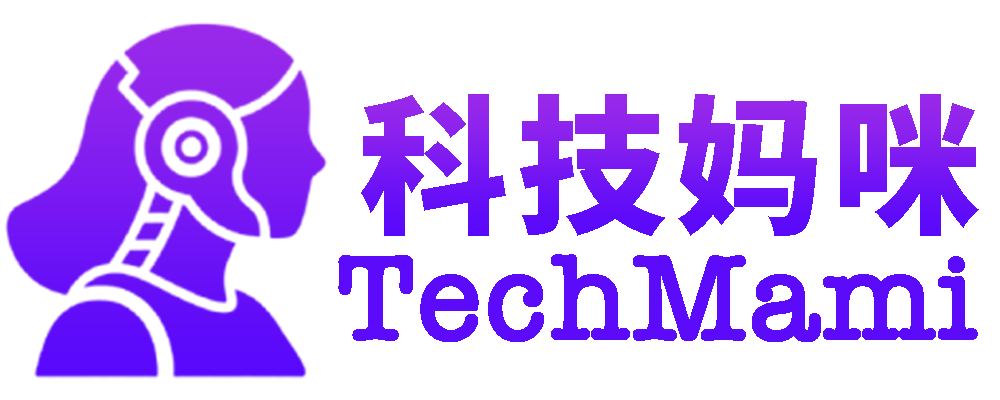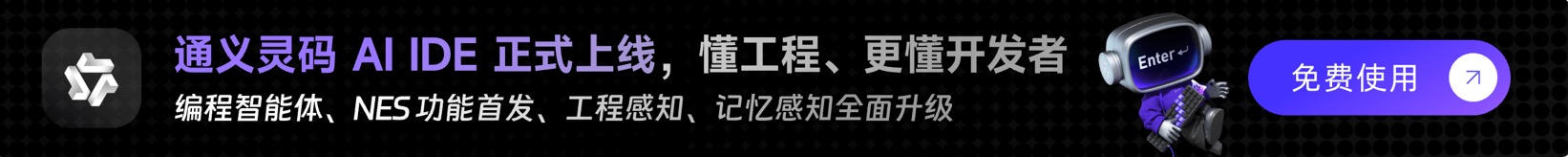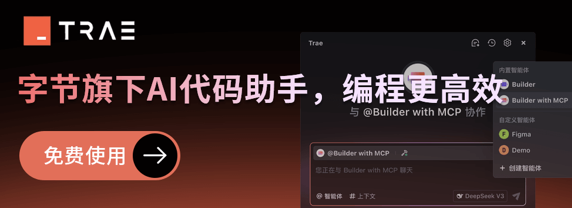说实话,我最近真的有点上头,每天都在跟一个叫Claude Code的AI工具打交道。你可能不知道,这玩意儿几乎把我的工作方式完全颠覆了。以前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Cursor里写代码,现在呢?我几乎是放手让它来干。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我自己也觉得挺魔幻的。
要说编程速度变快了吗?其实并没有。但我感觉每天多出了30%的时间,因为那些重复性的活儿都被机器包圆了。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就是在给它下指令、看书、检查代码修改之间来回切换。要是你在半年前告诉我,我会更愿意当个工程主管而不是亲自敲键盘,我肯定觉得你是开玩笑。可现在呢?我能去冲杯咖啡,项目照样有进展;甚至陪最小的孩子去游乐场玩的时候,工作还在后台继续进行。就在我写这篇博客的时候,Claude还在帮我做代码重构。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让我忍不住陷入沉思:人工智能到底意味着什么?说实话,我对未来越来越乐观了。很明显,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就像文章里说的那样,“人工智能这个精灵已经从瓶子里放出来了,再也塞不回去了。”就算我们现在停止所有进展、冻结权重、停止训练,那些已经存在的系统仍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
不过说实话,接受这种变革确实需要时间。作为一个工程师,我过去一直坚信确定性和工程技艺的重要性。刚开始接触AI工具时,我也曾犹豫过——就在两年前,我还坚定地认为AI可能会害死我妻子。但这两年的发展简直令人惊叹。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便我们现在止步于此(虽然看起来毫无可能),AI也已经成为大量创新和创造的基础平台。
你有没有发现,AI融入日常生活的速度简直前所未有?相比之下,智能手机的普及都显得慢了许多。通勤路上或喝咖啡的间隙,总能看见有人在跟ChatGPT对话。我甚至遇到过咖啡师、理发师、游乐场里的家长(那些我眼中并非“科技达人”的普通人)告诉我,AI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从写信、搜食谱到辅导孩子作业,无一例外。
但有意思的是,尽管AI的影响如此巨大,世界上大部分人还没真正接触到这些工具。很多社群、行业乃至整个经济体,都还没开始思考自己将被如何重塑。这种反差让人感觉有点诡异——一半是汹涌的革命浪潮,另一半却是风暴前的寂静。
更让我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么多技术从业者反而在抵制这股浪潮?托马斯·普塔切克那篇文章《我那些怀疑AI的朋友都疯了》说出了我的心声。它用幽默的方式精准戳中了我身边圈子里弥漫的AI抵触情绪。为什么那么多我在科技界敬重的人——工程师、开源贡献者——反而成了对这场变革最抵触的一群人?我们亲手创造了这么厉害的东西,很多人却非但没有好奇,反而报以轻蔑,甚至否认它的能力。
当然,AI带来的影响是真实而深远的。它迫使我们思考一些重大问题:比如教育。如果AI在教学、解释和课程个性化方面能胜过传统课堂,那我们熟悉的学校会变成什么样?如果孩子们从小就期待与智能体互动,我们该如何教导他们利用这种力量去推理、创造和协作,同时又不至于过度依赖呢?
从全球角度来看,AI的影响远超以往任何技术浪潮。它不像搜索引擎或社交媒体那样,让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美国的技术基础设施。AI更像是蒸汽机那样的奠基性突破,一旦问世,便成为历史必然,没有国家能承受被排除在外的代价。
所以当我一边给Claude分配任务,一边读一些有深度的内容时,我不禁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可逆转且影响深远的变革开端而感到兴奋。
我理解有些人为什么会变得愤世嫉俗或恐惧。程序员和艺术家的工作肯定会改变,但不会消失。我觉得作为程序员学到的所有技能,在搭配这种新工具后,反而变得更值钱了。同样,AI生成艺术的泛滥也让我更加下定决心要尽快雇佣一位优秀的设计师。人们永远会看重精心打造的产品。AI可能会一下子提高所有人的标准,但正是谨慎的思考和刻意的创造行为,才能让你脱颖而出。
当然,我保持乐观可能也有自己的理由。但用得越多,我就越相信乐观才是每个人更应采取的态度。善用AI能极大增强人的能动性。它能帮助我们跨越文化沟通,让知识获取大众化,加速医学、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创新。
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有点混乱和原始,但道路是清晰的:我们不再只是使用机器,而是与机器协作。虽然为时尚早,但我相信未来我们回望这十年时,会像过去的人们看待电或印刷术一样——不再视作新奇之物,而是一切改变发生的时刻。
让我们在那一刻来临之时,摒弃愤世与恐惧,带着炽热的好奇、沉甸的责任感,以及对那个必将到来、值得你我共赴的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迎接它!